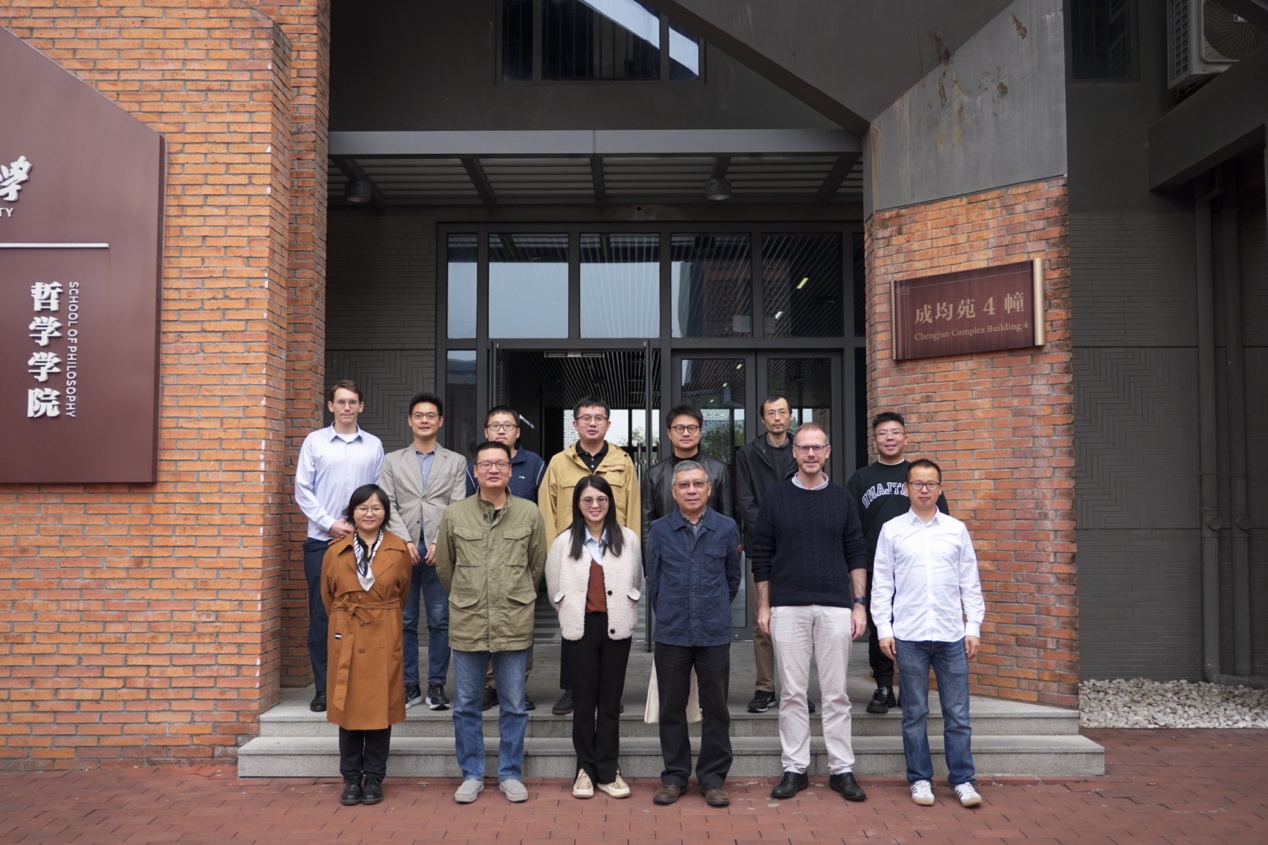2024年11月9-10日,“意向性、理解、视域(Intentionality,Understanding,Horizon)”德国现象学工作坊(Workshop on German Phenomenology)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浙江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的国内外二十余位学者与会参与讨论。
会议首先由浙江大学的倪梁康教授致辞,他向与会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在致辞中,倪梁康教授指出,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当重视德国哲学的当代向度,以及对哲学功用的反思。他认为,沿着这一路径,无论哲学以他人思想,还是以自身思想为线索,都会导向真正的哲学反思。



9日上午的报告由浙江大学的李忠伟长聘副教授主持。
同济大学的高松副教授作了以“类型和语音——普遍性与观念性的起源”为主题的报告。他指出,一切成为意识对象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了一种类型上熟悉的视域,而概念是语言化的类型,使我们获得超感性的知性能力。最终,形成了具有感性观念性、离散性和精确性、非时间性等特征的语言。

报告由东南大学的何浩平副教授评议。在评议中,他首先认可了高松老师对于现象学资源的综合运用。结合自身对于几何学起源的研究,他提出,“语音是第一个观念之物”、对多重观念性的区分等观点具有高度原创性,启发了对于“概念与本质”、“token and type”关系的思考。

同济大学的张振华副教授作了以“海德格尔与音乐”为主题的报告。他指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音乐处于一种贬低的倾向之中,并对比了德国古典传统、希腊传统中对音乐的论述。他考察了音乐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踪迹,并提出这表明了音乐在主题性考察意义上的“缺失”与无法逃开的“痕迹”。

报告由浙江大学的王宏健研究员评议。在评议中,他提出,语言本体论是否等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借助逻各斯来进行言语行为,但这不等于语言来源于逻各斯,相反,语言很可能来自于某种超越的不可说之物。

湖南大学的文晗副教授作了以“连续与断裂—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论事件”为主题的报告。他指出,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二人对基于事件为核心的历史观念的阐释,所针对的最大对手无疑都是黑格尔,但即便如此,列维纳斯对事件与历史的理解隐隐的仍然指向了海德格尔。这也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事件哲学”的脉络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线索。

报告由武汉大学的贺念副教授评议。在评议中,他提出,论文用连续和断裂概念把握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之间的差异,关注海德格尔思想概念演进的七个阶段。但问题在于,海德格尔的历史观究竟是谱系性的,还是一种范式的转换?

9日下午第一部分的报告由浙江大学的刘环特聘副研究员主持。
东南大学的何浩平副教授作了以“胡塞尔是轻易本体论者吗?”为主题的报告。他指出,简单本体论者认为:存在问题能够被轻易解决,从而不值得辩论。据此,胡塞尔对存在着纯粹意识的说明,也应该被理解为是轻易本体论式的。最后,他处理了关于这一立场的两个质疑:形式本质无法用轻易本体论来论证、对纯粹意识的存在性无法用轻易本体论来论证。

9日下午第二部分的报告由浙江大学的Christopher Gutland副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的Christopher Gutland副教授作了以“Husserl’s Discovery of the Horizon of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fter the Logical Investigations”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提出: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 Husserl sought to validate logical meanings through intuitive givenness. Initially, he conflated intellect with sensory intuition but later realized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perates independently. He ultimately embraced an idealism that linked intuition with the ideation of essences. This presentation argues that separating sensory and intellectual intuition introduces an intellectual horizon, distinct from spatiotemporal horizons, which can correct perceptual misassociations.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试图通过直观的被给予性来验证逻辑意义。他最初将智性与感官直观混为一谈,但后来意识到智性理解是独立运作的。最终,他接受了一种将直观与本质观念化联系起来的观念主义。该报告认为,区分感官直观和智性直观引入了一种智性视域,不同于时空视域,它可以纠正感知上的错误关联。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Prof. Sebastian Weydner-Volkmann作了以“Thoughts on Materiality in Postphenomenology: The ‘Latent Telic Inclinations’ of Digital Interfaces”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提出:As our world digitizes, Husserl’s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should extend to digital devices. Don Ihde argued that technology shapes experience, with different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mediating perception. Though technologies allow varied uses, their design influences how we perceive through them. This presentation suggests that Ihde’s focus on materiality needs updating for digital tech like AI and apps, proposing “quasi-materiality” to better capture how digital tools shape our perception. /随着我们的世界数字化,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应扩展到数字设备上。唐·伊赫德提出技术塑造体验,不同的人机关系会调节感知。尽管技术提供了多种使用方式,但其设计影响了我们通过技术的感知方式。该报告建议,伊赫德对物质性的关注需要更新,以适应AI和应用程序等数字技术,提出“准物质性”这一概念,以更好地捕捉数字工具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

浙江大学的Karl Kraatz讲师作了以“Heidegger’s Critique of the Presuppositions of Husserl’s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提出:Heidegger critiqued Husserl’s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arguing Husserl neglected its ontological dimension by focusing too narrowly on epistemology. Unlike many scholars, this presentation contends Heidegger’s critique is an immanent one, refining Husserl’s ideas into an ontological epistemology. This presentation explores this by examining Heidegger’s early writings on intentionality, the noema-noesis relationship, and the transcendental ego to show how he builds upon and deepens Husserl’s insights. /海德格尔批评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认为胡塞尔因过于专注于认识论而忽视了其本体论维度。与许多学者不同,该报告主张海德格尔的批评是一种内在性批判,将胡塞尔的思想深化为一种本体论的认识论。该报告通过考察海德格尔早期关于意向性、意向物-意向行为关系及先验自我的著作,展示了他如何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发展并深化其思想。

10日上午的报告由同济大学的高松副教授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的王鸿赫副教授作了以“实在之物本身可以变模糊么?重审胡塞尔的视觉感知理论”为主题的报告。他指出,胡塞尔认为意识方面的视觉域由二维的感觉材料构成,而意识对三维物体的构造据此也即是对一个超越出意识之物的构造。由于视觉感觉材料一般不可通达,以及这种理论陷入了“图像论”困境等原因,使得该理论面对的更多的是批评和拒斥。他从视觉感知的直观出发,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描述原则,指出胡塞尔视觉对象构造理论的症结所在,给出一个更合理的视觉感知理论。

报告由浙江大学的宋文良博士后评议。在评议中,他提出,文章需要处理物与视觉感的关系、空间感与身体的关系等问题。胡塞尔的构造理论指出,构造依赖于身体器官,但我们仍然可以思考,身体在构造活动中是否必要。如果空间依赖于身体,那么身体在还原后是否需要保留?

同济大学的尚静助理教授作了以“A Re-evaluation of Henry’s Criticism of Husserlian Intentionality”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提出:On the one hand, even at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of the subjective body, where Henry would pretend to pinpoint a radical immanence, that is, an auto-affection, there is already – although he chooses to side-line it – a transition between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an implication of a transitivity between (archi-)passivity and activity in Henry’s enlargement of auto-affection into an incarnation as the generation of life. /一方面,即使在主观身体的原初构成问题的核心,亨利试图指出一种根本的内在性,也就是自我感受,但其中已经存在一个从内在性到超越性的转换——尽管他选择将其搁置;另一方面,在亨利将自我感受扩展为一种“生成生命”的化身过程中,(原)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也隐含着一种跨越性。

报告由湖南大学的文晗副教授评议。在评议中,他认为,文章内容丰富,关注不同层级的超越性概念,发展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他进一步借助德勒兹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阐发,提出瞬间性的抵抗对单子自身构造作用的层级问题。

四川大学的唐章梅博士后作了以“显现、意义和记忆:透过海德格尔视角的阿伦特关于公共政治 空间的生存论解读”为主题的报告。她指出,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建构隐晦地借用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以古希腊城邦(polis)为基本范式,阿伦特确立其未明确言明的公共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即,公共领域作为显现的意义空间。

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勇副教授评议。在评议中,他提出,阿伦特的确在政治哲学方面收到海德格尔深入的影响,但文章所依据的文本并不典型,应该考虑《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阿伦特显然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我们应该重视二者思想的差异之处。

最后,由浙江大学Christopher Gutland副教授进行闭幕致辞,他向与会嘉宾表达了诚挚感谢。在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中,会议圆满结束。